英倫漫話/局外人\江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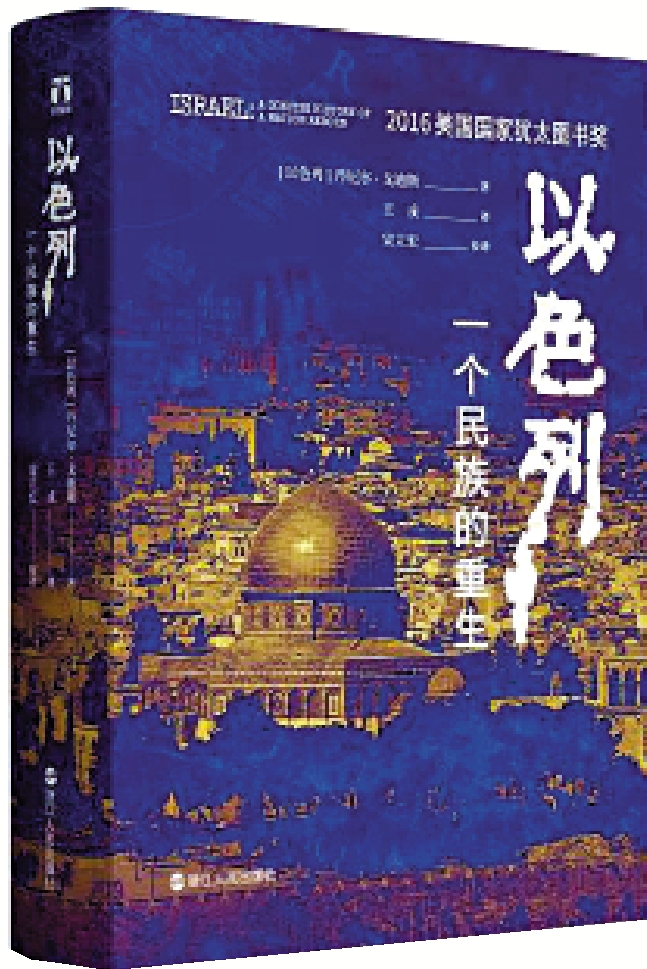
早前內地新上映的德國電影《誰偷了我的粉兔子》,講述了猶太女孩安娜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漂泊異鄉,戲裏的情節感人至深,而戲外的故事同樣令人唏噓。
影片改編自英國女作家朱迪斯·克爾的同名自傳小說,她出生於戰前德國的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片中的流亡經歷正是她一家人的遭遇。與電影採用悲傷中帶着溫情的表現手法不同,現實中的一切無比殘酷,九歲的克爾跟隨父母顛沛流離,路上經常食不果腹,還要時刻提心吊膽,最終輾轉了五個國家才落腳英國。用克爾在書中的話說,「沒有人會因為好玩而流亡他鄉,人們深愛自己童年待過的地方,那裏的人,那裏的語言。」而她之所以飽經磨難,皆因她是一個猶太人。
實際上克爾在英國落腳後,社會氣氛未有本質改善。當時納粹思潮在英國盛行,不僅有很多納粹黨人的信徒,就連王室都與納粹有着扯不清的關係,像「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就被指充當納粹德國的間諜。英國許多貴族和社會名流更與納粹關係密切,美國耶魯大學學者勞倫·楊在《希特勒女孩:二戰前夕的英國貴族和第三帝國》一書中,就講述了年輕貴族尤妮蒂的真實個案,她本人迷戀希特勒,是一名激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為了見到希特勒,她還入讀了德國南部的一所精修學校,她後來得以和希特勒見面一百六十多次,湧動於英國上流階層的親納粹狂熱可見一斑。
甚至連英國政府對猶太人也缺乏同情。猶太作家丹尼爾·戈迪斯在《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一書中直指,二戰期間英國負責託管巴勒斯坦,但在戰爭最初的十九個月中,沒有批准一名猶太移民進入該地區。不僅如此,英國為防止猶太移民潛入,還專門建立了拘留營,和納粹德國一樣將抓住的猶太人,統統關進有鐵絲網的營地。據說戰時首相邱吉爾亦對猶太民族沒什麼好感,劍橋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托伊曾在學校檔案館中,發現一篇他寫於一九三七年的文章《猶太人如何才能抗擊迫害》,他在闡述席捲歐洲的反猶浪潮時聲稱,「或許他們(猶太人)也應該為自身所遭遇的災難負部分責任」。這也就不難理解,邱吉爾為何一度登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暗殺名單。
正如英國學者卡爾德·沃爾頓在《帝國內幕:英國情報機構、冷戰和帝國的黃昏》一書中所說,老牌帝國與猶太民族的關係並不和諧,想知道英國人緣何對猶太人反感,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早在十一世紀歐洲「征服者」威廉入侵英國,猶太人便隨之而來,基於宗教等複雜因素,猶太人多以放高利貸為生,加上後來歐洲十字軍東征運動等政治迫害,英國人對他們的偏見和敵視與日俱增。比如理查一世時期,倫敦的猶太社區遭到大洗劫,許多普通猶太人被屠殺;到了愛德華一世時代,他又對猶太人下達「逐客令」,所有猶太人必須限時離開英國,否則將被處死。甚至直到十九世紀,英國各階級也常將猶太人視作異教徒,並未給予他們相應的公民地位。
英國這種瀰漫的反猶情緒,也在文學作品中有所記載並可一窺端倪。像莎士比亞筆下《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便是貪婪的猶太奸商;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大反派和邪惡象徵的教唆犯斐今,也是陰險毒辣的猶太人。甚至以童書《查理和巧克力工廠》聞名的達爾,也聲稱「希特勒不是無緣無故找猶太人麻煩」。如同英國學者西塞爾·羅斯所形容,對猶太人的偏見根深蒂固,注定了他們在英國只是被利用,「似乎就是一塊吸滿了王國流動資本的海綿,每當國庫國虛時,就要去擠這塊海綿」,根本擺脫不了被歧視的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猶太裔的本傑明·迪斯雷利破天荒地擔任了英國首相,但背後付出的代價卻鮮被提及,他不僅為此改變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更去掉了猶太姓氏,在他剛從政時因猶太人多從事舊衣買賣而被人蔑稱為「舊衣服」,即便他成為首相後,外界仍質疑他是否對英國足夠忠誠。事實上,直到將近二十世紀,猶太男性才獲得與其他英國白人男性完全一致的政治權利。
進入二十一世紀,英國社會日益政治化,猶太人的處境變得更為複雜。二○一六年發生了著名的倫敦市長選舉風波,有工黨女議員因不滿以色列的中東政策而被批反猶,工黨前倫敦市長利文斯通站出來為其辯護,指「以色列人在批評納粹的同時,他們也在對巴勒斯坦人做同樣殘忍的事。以色列游說團體長久以來精心布局,令如今只要有任何人批評以色列政策就被視為反猶太人。」豈料他這番話遭到不同政治立場人士的集體圍攻,以至於有評論指,他們並不關心反猶本身,更像是把它當作選戰工具。另外,在英國脫歐期間,有極端民粹主義分子公然佩戴納粹時代侮辱猶太人的「大衛星」標誌。
直到今天「反猶」仍是英國社會的高頻詞,有社會學者就認為,猶太人的遭遇是冰山一角,顯示英國社會遠不如宣稱的那樣多元和包容,猶太人和許多其他少數族裔一樣,儘管努力融入當地,卻始終有如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