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獅是神誕節慶中的助慶環節,亦是一種表演。「獅」由紙紮獅頭和布制獅身組成,傳統的獅頭主要以竹篾和紗紙紮作而成,外型分為南獅和北獅兩類,而南獅又有佛山裝、鶴山裝和佛鶴裝等樣式。紮作獅頭工序分為「紮、撲、寫、裝」,即紮作、撲紙、寫色、裝飾。獅頭紮作在香港已有悠久的歷史,村落舉辦神誕活動時,會以醒獅或其他瑞獸助慶,獅頭紮作因此應運而生。

許嘉雄出生於一個武館家庭(南派武術),全家都從事舞獅,舞獅非常看重獅頭紮作,於是許嘉雄自幼便接觸舞獅與獅頭紮作,如他自己所言「我從6歲開始就很喜歡舞獅,因為本身我家是武館家庭,我的父親是打拳,我爺爺、我叔叔和伯父也是練拳術、舞麒麟的,所以我對舞獅頭、舞麒麟很有興趣,從小到大,可能在媽媽肚子裏就已經很喜歡這件事,整個人生都是舞獅與紮獅,我讀書讀得很少,因為我全心全意去紮獅頭」,紮獅頭是許嘉雄一生堅守到底的事業。
01.「中毒」般喜歡獅頭的那些年
六歲開始學習紮作,十一歲紮出人生第一個獅頭,後不斷精進技藝和打工積攢資金,創立了「雄獅樓」,到今天,已與紮獅頭相伴三十餘年。許嘉雄形容自己喜歡紮獅頭,就像「中了毒一樣那麼喜歡」。
因家中武館只舞鶴家麒麟,兒時的許嘉雄便和夥伴們到其他的武館學舞獅,和紮作的緣分則起源於那顆被鐵箱鎖起的獅頭。許嘉雄說:「80年代至90年代來說,全新的獅頭很貴的,我記得是約一萬元吧。小師弟如我怎會有機會接觸到啊!我們只會接觸到破爛的舊獅頭。」年僅六歲的許嘉雄便把那些舊獅頭拿去拆,拆了又砌,砌完又拆,玩着玩着倒也玩出樂趣來,大概十一歲就做出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個獅頭。
十三歲那年,他自覺不愛讀書只愛紮獅頭,便退學並到上環紙紮鋪拜師學藝。當時他向紙紮師傅黃佳學藝,短短十數日的速成課,對許嘉雄來說卻意義重大。此後他在紙紮鋪打工,白天做紙紮,晚上回家練習紮獅頭。許嘉雄在家痴迷般地紮獅頭,家中遍地都是獅頭,獅頭最多的時候,他甚至把床板拆了來放獅頭。這一紮便又是二十多年。

02.從「紙紮佬」到真真正正的紮作藝術家
許嘉雄剛入紮作一行時,師傅就提醒他,最好早些轉行,這一行被人們叫做「爛棉蠟」,沒什麼機會與前途。剛開始打工紮作時,許嘉雄十一歲,工資是一百五一天;十三年後,許嘉雄成為了紮作大師傅,他的工資還是只有四百元一天,足夠溫飽卻沒有盈餘。直到妻子在壽司店找到了一份月收入一萬二千元的工作時,許嘉雄才發覺自己九千元的月收入與自己磨練多年的技藝不對等。恰好當時許嘉雄接到了一個項目,賺了一萬多元,這讓他下定決心開始單幹。
近年獅頭紮作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推動行業為更多人所熟識。許嘉雄說:「以前形容我們是紙紮佬,是社會上好低微的的人才會做我的工作的,現在慢慢你會看到,開始有人形容我們是紮作藝術家啊!」列入非遺給了獅頭紮作更多的平台與空間去發展,許嘉雄在身體力行示範如何傳承文化的同時為行業帶來革新,獅頭紮作的方式仍是傳統的「紮、撲、寫、裝」,而創造外形上注入了更多巧思。
許嘉雄偶然發現太太指甲油裏的銀粉很漂亮,便將其加入獅頭中,這是從前不曾有的創作,而許嘉雄一做便人人效仿,現在銀粉已成為獅頭中必有的元素。許嘉雄表示,製作和生活息息相關,製作是沒有規定和限制的,任何一樣東西都可以做。早幾年許嘉雄還曾經和一個泰國的藝術家合作做一隻獅子,其花紋與塗鴉方式都與傳統獅頭大不相同,是一隻很潮的「獅王」。許嘉雄希望整個行業繼續往藝術方面走,他與很多藝術家合作推出裝置藝術品,其中一件是在美國舊金山市用紮作技藝創作六個大花瓶。他的紮作在保留傳統技巧的同時多加創新,越來越新潮,越來越藝術。

03.一路「紮」下去,進軍國家級非遺
談到自己在推廣紮作藝術方面的使命,許嘉雄直言希望做到葉問那樣,提到「詠春拳」便要想到葉問,提到「紮獅頭」便要想到許嘉雄,成為紮作行的一代宗師。因為自身經歷過學習紮作最困難的階段,他開創工作坊,免費教授紮作技藝,希望能把自己學到的分享給年輕人,分享給對紮作感興趣的人。
自幼愛上舞獅,他在學習紮獅頭的路上幾番碰壁,經歷不堪回首的學徒歲月,再偶然地在十七歲成家立室,為了生計日夜顛倒地趕製紙紮品,到後來自立門戶,創辦屬於自己的的工作室「雄獅樓」;再後來,他的作品流傳海外,又再後來,紮作被列為「非遺」。「紙紮佬」忽然身價暴漲,也成了藝術家,紮作之路跌宕起伏,這是他人生的傳記,也是獅頭紮作行業的寫照。未來,許嘉雄還會繼續推進工作坊建設,讓更多人了解和學習獅頭紮作技藝,用堅守與巧思活化獅頭紮作,在推廣紮作藝術與非遺文化的道路上一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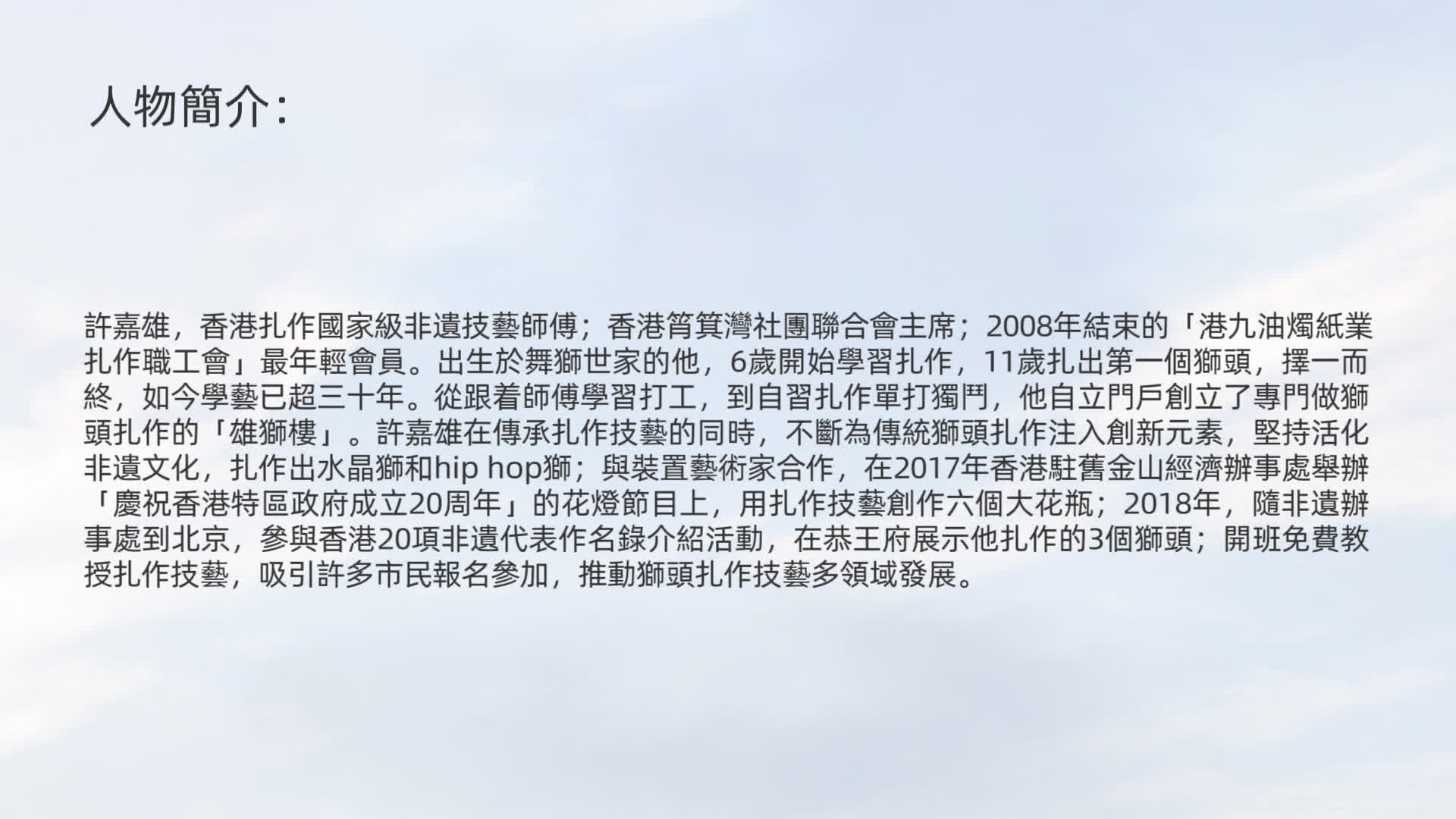
(暨南大學《灣區拾遺錄》系列作品摘選)
相關推薦新聞鏈接:
死生契闊•手作傳情 1| 紙紮師許嘉雄:願做疫情下「逆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