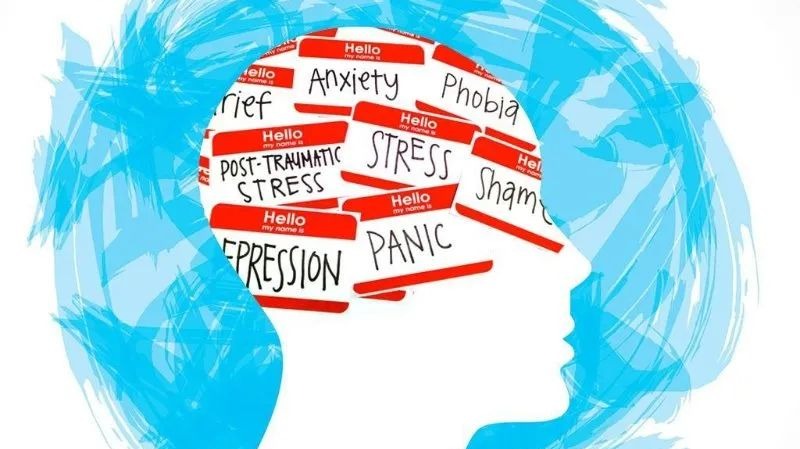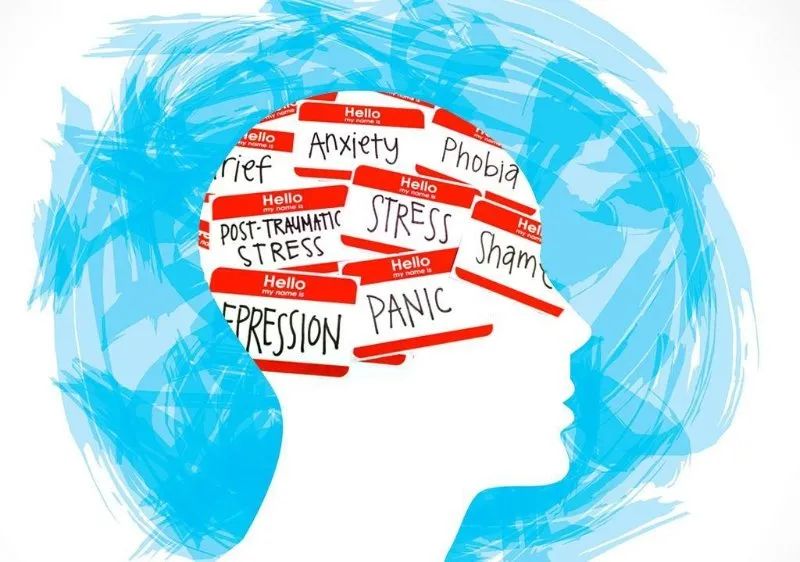
文/王越
作家克萊格·泰勒因寫《倫敦人》一書出名。其中,他寫了一個悲傷輔導師的故事,在倫敦建立了援助中心,專門幫助創傷應激障礙者。
他幫助那些成年人度過了人生的至暗時期。
在杭州一家大學所屬的三甲公立醫院,我做着同樣的工作,不過,幫助的是兒童和青少年,這些孩子幾乎都出生於2000年以後,我陪伴他們度過生命早期的傷感與低谷時間。
在中國,心理諮詢處於起步階段,面向兒童青少年的心理諮詢幾乎是空白。
2017年10月,我加入了由心理學博士、主任醫師駱宏教授創建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聯合門診創始團隊,這是由精神科醫生和擁有教師、記者等多學科背景的心理諮詢師共同組成的專為孩子們提供心理幫助的聯合門診,我喜歡這份有意義的助人工作。
時光如靜水流入了2021年的10月,面向兒童青少年的臨床心理諮詢實踐,已經整整四年了。
四年,一個大學本科讀完了,我覺得可以寫點什麼了。
先說一組數據吧,它來自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最新版《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在被調查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樣本中,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鬱的檢出率為17.2%,重度抑鬱為7.4%。
- 小學階段的抑鬱檢出率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約為1.9-3.3%。
- 初中階段的抑鬱檢出率約為3成,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為7.6%-8.6%。
- 高中階段的抑鬱檢出率接近4成,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為10.9%-12.5%,抑鬱的平均水平隨年級的升高而增加。
很多人奇怪,為何現在的小孩子會得抑鬱症?四年的臨床心理諮詢發現,城市中的00後一代和以前的孩子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全都是在互聯網下長大的,他們人人有手機,比如在知識信息搜索方面和家長老師是同步的,甚至更快,如果讓他們選擇網絡世界還是現實世界,他們會更喜歡前者。但由於年齡尚小,心智尚不成熟,情緒難以自控,在不被周圍成年人理解的現實壓力面前,他們就會呈現出抑鬱、焦慮等病理化的症狀。下面就講講他們的故事。
「低齡化躺平」的孩子
2021年有個很熱的詞叫「躺平」,對於正在讀書的00後們來說,學業壓力是現實生活中的第一壓力,對那些厭學不肯去學校讀書的孩子我稱之為「低齡化躺平」。
今年就來了好幾個「躺平」的孩子,有高中生、初中生、也有小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只有8歲,生於2013年。
他說爸爸在外地工作,媽媽沒有工作,管他和雙胞胎姐姐,姐姐成績很好,他的成績很差,媽媽總是表揚姐姐,總是罵他打他,老師也不喜歡他,「學校沒意思,我不想去學校!「
這個8歲的小男孩其實是一個聰明有想法的孩子,有向上向好的動力,只是被不良情緒給「困」住了,這和媽媽的養育方式有關。男孩和女孩天生差異比較大,尤其是小學低年級階段很多方面的表現不如女孩,媽媽卻總是拿姐姐做參照,男孩的表現越來越差,並且再也不肯去學校,媽媽打他罵他吼他都沒有了作用,絕望中只好帶他來到了聯合門診,被診斷為抑鬱情緒。
和媽媽的反饋與晤談構成了第一次諮詢的後半部分。
後來的諮詢中,小男孩告訴我,媽媽變了,不打他不罵他不吼他了,允許他踢足球了,還讓姐姐給他補習功課。第四次諮詢時,小男孩情緒好多了,說去學校參加月考了,成績出來了,進步了,老師在全班表揚了他,他願意去學校讀書了。
厭學「躺平」的孩子,都是父母已經沒有辦法後帶他們來聯合門診的,來之前,他們通常都認為是孩子自身的問題,最出乎他們預料的是,諮詢師和孩子交談完後,也會和父母晤談,希望父母在和孩子互動方面、語言溝通方面、教育方式方面做些調整或改變。
為了孩子,父母們通常也會反思原有的互動模式,父母的變化孩子也看在眼裏,會被觸動,孩子也會跟着改變了。
在一個家庭系統裏,一個人的小改變,往往會帶來整個家庭的大變化。
但不是所有的諮詢都令人鼓舞。

有個高一女孩成績墊底選擇「躺平」,每天待在家上網刷劇打遊戲。她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和父母不親,甚至直呼他們的名字。她說自己不想諮詢,是被父母逼來的,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還有一個已經在家裏「躺平」一年的孩子,來諮詢前突然反悔不來了,在諮詢室裏夫妻雙方對孩子的現狀互相指責,甚至吵了起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厭學成因複雜,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層面都會受到影響,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在學習過程中沒有甚至很少得到家長和老師的正向反饋,感受到的幾乎都是負向的不愉快的情緒體驗,於是,或逃避學習,或沉溺遊戲也就成了一種必然選擇。當然,還有不少是家庭系統出了問題,那麼首先要解決的是親子關係問題、夫妻關係問題,而非父母想要解決的何時去學校讀書問題,這需要家庭系統內部原有關係的重新建構。但對於被父母逼來自己並沒有諮詢意願的孩子,或者只是父母來孩子不肯來的孩子,我也深感無力。
被人際關係困擾的孩子
來聯合門診的孩子,不少被診斷為抑鬱、焦慮情緒,除了學習壓力之外,人際關係問題是困擾他們情緒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人際關係,包括和父母的關係、和老師的關係、和同學的關係。
很多成年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也頗感頭疼,何況缺少社會經驗的孩子。
來訪者生於2010年,是一個11歲的女孩,稱她為小梅吧。
小梅進入小學高年級後,因品學兼優,由學習委員被選為班長。據媽媽說,因為一件小事,女兒已經兩周沒有去學校讀書了,家人怎麼勸都不聽,勸多了就會不停地哭,還失眠,胃口越來越差,精神萎靡。
爸爸媽媽一起帶她來到聯合門診,被診斷為抑鬱狀態。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原來小梅被選上班長後,以身作則,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得到班主任老師的肯定和多次表揚。
有個女同學是小梅的好朋友,兩人形影不離,一次同學和小梅反映,每次輪到這個女同學做值日組長,她都是指揮別人搞衞生,自己從來不動手。小梅就把同學的意見和女同學反饋了,希望她做值日組長時和大家一起搞衞生。結果,女同學卻到班主任那裏打小報告說小梅值日都是袖手旁觀。
小梅得知後氣壞了。班主任了解情況後,批評了那個女同學並讓她給小梅道歉,還了小梅公道。班主任認為事情解決了。但小梅心裏還是不舒服,回家和父母說了後,父母說,多大的事啊,人家已經道歉了,原諒對方,繼續做好朋友唄。小梅聽了父母的話不但沒有感到安慰,反而大哭起來。
面對情緒低落的小梅,我理解她被好朋友刺傷的心痛,了解到小梅心裏其實很矛盾,不捨得失去多年的友情,但又無法原諒女同學的做法。
通過我們之間的對話,小梅釐清了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第二次來諮詢時,小梅開心地告訴我,她向班主任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後,班主任專門找女同學談話了,告訴她口頭道歉是不夠的,需要拿出行動來獲得小梅的諒解,才能重新做好朋友。
一周以後,小梅再次到來時告訴我,女同學用實際行動表明了歉意,她也從內心原諒了女同學。
在這次事件中不難發現,成年人在處理孩子人際關係問題時考慮的比較簡單,容易將成年人的評價方式放在孩子身上,認為孩子之間不過是芝麻大點的小事情,不太重視。
其實,孩子心裏無小事,大人眼裏的小事可能就是壓垮孩子心理的最後一根稻草。前年上海盧浦大橋上,開車的母親因為兒子在學校和同學發生了矛盾,不問清緣由就在車裏對兒子進行嚴厲批評,導致男孩情緒失控,拉開車門,跳橋身亡。
當我們無法了解孩子的內心,自以為是的「正確教育」極有可能適得其反。
再說說一個男孩的故事。
男孩生於2012年,讀三年級,媽媽說兒子成績不錯,但又頹喪地說這些年來他們被兒子折騰死了,經常被叫到學校,又打了某某同學了,又去拉前排座位女同學的辮子了,某某同學又告他狀了。
這個男孩的成長過程是在外婆主導的大家庭中長大的,家人對他的養育模式就像紅樓夢中的寶玉,被祖輩溺愛,闖了禍後會遭受爸爸一頓暴打,外婆則護着寵着,到了學校,他希望同學們喜歡自己,卻不知道如何與同學相處,無意識地複製了家庭中的模式,調皮搗蛋,但學校並沒有寵他保護他的「外婆」,帶給他的全是人際挫敗感。
心理學家阿德勒說,一切矛盾全在於人際關係之中,只有做到課題分離,才能獲得自由。如何做到課題分離?祖輩參與育孩的家人之間如何做到有溫度、有親情與愛,又有邊界、有規條?這是作為孩子監護人的父母需要反思的,也是需要學習與成長的功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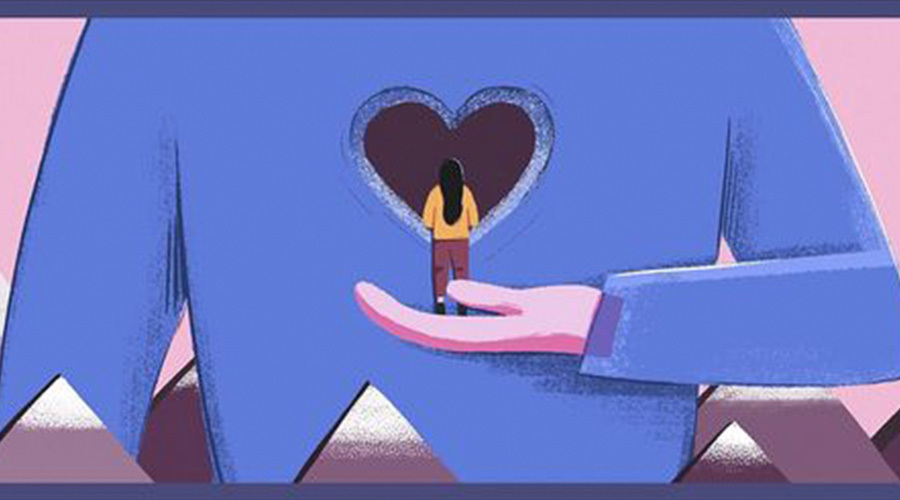
為情痛苦的男孩女孩
青春期是孩子的身體覺醒時期。
身體開始覺醒令孩子有了性意識的萌動,這是孩子成長的必經階段,他們對自己從哪裏來這個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也有了個人情感需求。
來訪者是一位自殺未遂被診斷為抑鬱症的男孩,生於2005年,16歲,神情沮喪地坐在我的面前,他喜歡上了班裏一個女孩,女孩也喜歡她,他們戀愛的消息被老師知道了,告訴了家長,女孩家長反應激烈,媽媽不許女兒和男孩接觸,並要求男孩家長管好自己的兒子,不要影響自己女兒的學習。
女孩是個聽話的乖乖女,自此不再搭理男孩。男孩無法理解女孩為何突然「無情地拋棄了自己?「他希望和女孩當面談談,結果女孩躲開了。他太痛苦,像一隻被關進籠子裏的困獸,開始失眠,情緒越來越差,直到有一天吞下了大把安眠藥。
坐在諮詢室時,距離他吞藥被父母發現後到醫院洗胃已經三四天了。
經過幾周的諮詢後,他主動說可以結束諮詢了,說自己想通了,放下這件事了,重新回到了學校讀書。
心理諮詢是心靈之間的對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這個過程也讓你好奇,有時候你不知道這些抑鬱的孩子是藥物起了作用,還是哪句關鍵的話起了作用,或者兩者共同起效了,有些孩子會在某一天突然想通了。
其實,孩子才是解決自己問題的專家,只是來諮詢之前,他們並不知道解決問題的那把鑰匙就藏在自己身上,通過藥物與心理諮詢的聯手干預,他們最終找到了那把打開心門的鑰匙。
再講一個也是因為情感問題想不通,割了手腕的生於2004年的女孩,高中生。
在諮詢室,看着她白皙的胳膊上一道道劃痕,令人心疼。
這個女孩暗戀一個男生很久,終於有一天鼓足勇氣向男孩表白,結果被男生婉拒,男生說自己心裏已經有人了,女孩問是誰,男生卻不告訴她。女孩開始失眠,上課總是走神,注意力下降,動不動流眼淚,用小刀劃自己手腕,有一天被媽媽發現,大驚,被帶到了聯合門診。
在少男少女的自我意識裏,自己喜歡的人也應該喜歡自己,一旦被對方拒絕,就會陷入學習成績下降,上課沒精打採,活着沒意思等負性情緒之中。有個媽媽說初一的女兒網戀,她不敢反對,害怕想不開,她只能給女兒提了兩個要求,男孩情況告訴她,如果要見面,她必須陪同。
這些來諮詢的00後的孩子普遍敏感細膩,把感情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他們太需要被理解被看見被懂,在周圍親人中找不到安慰甚至被指責被辱罵被打擊時,他們大都會產生極端的想法。來到諮詢室,起碼有個人願意傾聽,傾聽也是一種療愈。
無意義感、孤獨感的高智商學霸
來訪者生於2003年,讀高三,成績很好,屬於學霸級,父母說考上重點大學應該沒有問題,男孩也認同父母的看法,不願在學校一遍遍刷題了,選擇自己在家裏複習,但有時候會說活着沒意思之類的話,父母擔心其心理狀態,建議做做心理諮詢,他表示同意。
男孩在諮詢室坐下後,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沒有心理問題,只是覺得生命挺沒意義的,希望能夠聊聊這方面的話題。
無意義感是不少高智商孩子的普遍困惑,北大心理專家徐凱文教授曾經說一些孩子患了「空心病」,他們聽話自律,成為人們口中的「好孩子」、「優秀生」考進了北大後,卻失去了目標,不知道活着的意義,內心空洞苦悶。
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貫穿人的一生,是需要不斷思考的哲學問題,00後的孩子們比他們的父母一代更早地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
最終,在諮詢室,這個感覺到生命沒有意義的男孩通過每周一次的對話與討論,看到了以前被忽視的內心隱秘的角落,那個真實的自己,並認同生命的意義是由無數瞬間構成的,是創造出來的,是在與過去和未來、與自然和事物、與人和人之間互動中尋找的。
生於2006年,相貌清純的學霸女孩前來訴說的則是孤獨,因為班上女同學們喜歡看耽美小說,而她一點也不喜歡,倍感孤獨。
她手裏拿着一本詩集,是上個世紀80年代幾個著名詩人的詩歌總匯,其中有舒婷、顧城的詩,他們是上世紀80年代最火的詩人,是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這個05後女孩在讀他們的詩歌中產生了精神共鳴,感覺到被治癒,但同時又陷入沒有知音的孤獨。
精神上的孤獨感可以說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情緒,當沒有人可以產生精神同頻的時候,孤獨感就會油然而生。
都市裏的00後這一代尤其是獨生子女們,是帶着天生的孤獨感而來的,他們從小就有自己獨立的房間,意味着獨處的時間會更多,獨處會讓他們思緒更多,也會品嘗到孤獨的滋味。
心理學家安東尼·斯托爾說,想像力總是在孤獨狀態下展開翅膀,能夠享受孤獨的孩子才有可能培養出創造潛能。哲學家康德說的更直接,我是孤獨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
「是的」,女孩說,「孤獨讓人清醒,會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也可以體會到專註力,學習可以達到忘我的狀態。」女孩還提到了一本書,《夜航西飛》。
這本書我知道一點點,好像說的是一個女孩小時候跟隨父親到了肯尼亚,面對生活中無盡的孤獨還有危險,她始終活在自己的熱愛裏,最終成為非洲第一個職業女飛行員的故事。
女孩說,是的,這本書也給了她力量。
孤獨像是一個負面詞,通過我們的合作對話,女孩找到了它的正面意義,並且決定一步步去實現自己的考學目標。
她希望將來能夠成為一名不平凡的女性。
女孩的夢想深深地觸動了我,也讓我想起了著名心理學家Harry Korrman所言:最棒的諮詢是,在當事者走出諮詢室的那一刻,忘記了諮詢師是誰,只記得自己的目標、優勢與如何前進的方法。

而我,也從這份幫助孩子們的工作中找到了價值,豐沛了自己的人生。
(為保護隱私,文中個案信息已經做了處理,如有雷同,請勿對號入座)
來源:微信公眾號「 朱老師私塾」